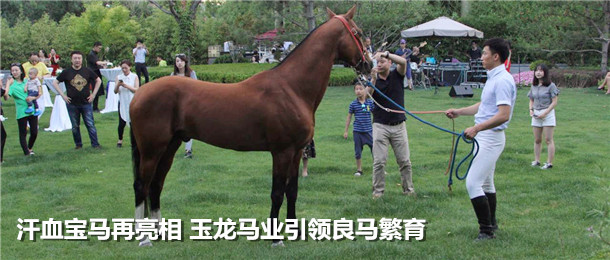“我看未来二十年”之刘益谦专场:收而不藏 贵(3)
发布时间:2014-04-28 12:21 【来源:成都商报】
前两天,我看了一则新闻,这新闻里面讲的是一个北京一个媒体人,公开起诉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丹霞。我看了声明,这个声明里这样写的,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丹霞在微博上用了一个名字到处谩骂,凡是支持《功甫帖》的她就到处乱骂,同时我也看了这边她骂,那边她用自己的名字写,发的微博是正常的。她特别是有一句话,我真的要凌乱了,她说,人品是最高学历。这样的人她还讲人品,现在被人家告了,法院也受理了。法院受理,我觉得首先是搞清楚了这个人是不是杨丹霞,甚至杨丹霞老师还用苦肉计,怕我不知道,还@我,我感觉是没法理解她是什么心情,是什么样的人。
中国字画的鉴定,特别是古代字画的鉴定,这么多年从古到今,我认为我们的鉴定一直是用目鉴鉴定的。目鉴是凭经验,原来那些老先生还在的时候,他们相对来说,我认为这些老先生的经验比较丰富,全国各地,甚至这些老先生参与了很多收藏,从他的实战性和他的研究来说都比较全面,加上这些老先生基本每个人都会画画,他们是艺术家,他们具备了目鉴的水平。从这角度来说,我认为他们具备了一言九鼎的鉴定的权威性,当然这个过程中间也不能说他们百分之百是正确的。到今天,我感觉我们这个鉴定是比较麻烦的问题,今天这个专家,明天那个专家。前两天我碰到上海有一个人办展览,这个人几年之前还采访我,现在不用了,不写文章了,自己搞了一个画室,他也画画,关键是他还卖画。画的东西,我感觉我学两年肯定不比他差,这个艺术品现在利益比较大,大家都感觉在利益面前很难把握住自己,那鉴定也一样。特别是我看前两天,还有一家报纸,为《功甫帖》的事情当时采访了上海博物馆的钟银兰老师,说刘益谦2月18日邀请你们到北京现场观摩《功甫帖》是不是“双钩”的,你们为什么不去,她说我们有事不想去,又有记者问她,你没有看作品怎么知道是双钩的。她说了一句,可能我这辈子忘不了的话,她说别人不看原作能说不是真的,我为什么不看原作不能说是双钩的。已经到这种情况下,如果上海博物馆这三个研究员不是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员,如果上海博物馆不是通过学术的方式跟我讨论《功甫帖》,我认为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动静,我也没有必要。我认为我感觉就像我睡觉一样,一个蚊子在我耳边飞过去,我手挥一下我根本不会耽误事情,但是这个蚊子一直在你耳边一直叫,让你睡不着觉,那你没有办法,只能开灯想办法把这个蚊子拍死,我认为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它就一直跟你叫,叫一次不够,手挥两下它还在,那你只有爬起来非把它拍死不可。

鉴定我认为也是这样的,鉴定现在特别混乱,所以我感觉这样的状态下,我们美术馆的一些我认可的专家也好,包括一些体制内的和海外的专家,可能人家对于上海博物馆这样一个身份不便于公开出来,大家都在围绕鉴定究竟应该怎么做进行讨论。2月18日,我感觉还不是说希望通过《功甫帖》来一个新的话题。在中国除了目鉴的鉴定,能不能借用现在科学的方法?现在这个科学的方法也不是什么高科技,只是用放大镜放大,通过对纸张的对比来做。2月18日我们现场做的这样一个演示,从效果来说我也看到了很多人说,今后传统的目鉴会受到冲击。的确是这样,我认为今后在鉴定方面,一个我们要看一件作品的传承。比如说《功甫帖》,买一件作品还是要从它的流程传承着手,我感觉我今天做不到,我也没办法证明《功甫帖》百分之百是苏东坡写的,我只是说这件作品无限接近苏东坡,但是我可以很简单的驳斥上海博物馆的观点,因为“双钩”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同样我认为一件古老的作品,谁都无法证明它就百分之百是真实的。苏东坡死都死了一千年左右,谁来证明,除非他爬起来,谁都证明不了。我证明不了,上海博物馆同样,馆藏的东西它也只能说按照传承这东西是谁的,他也没办法证明的。我有一次在故宫去看,边上有两个人说故宫的全是假的,这个话大家说一句假与真特别简单,不要说东方的艺术,西方也一样。谁能证明达芬奇的作品百分之百就是达芬奇的,谁都没有看到过达芬奇画画,看到达芬奇画画的人都死了,只能按照传承进行说明是不是达芬奇的。
有很多人认为我没有买艺术品,中国的艺术品可能就两千块钱一张,五千块钱一张,他们可以继续收藏,我认为因为有这种观点所以造成了“东亚病夫”。全世界的艺术品都一样,除了在博物馆以外,这种传世名著在博物馆以外,好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国外,要么在西方大家庭,要么有钱人手上,都一样的。
《功甫帖》这个事件出来以后,我感觉网民还是很关心我的,突然有一天网上出来一个东西,找出来一封资料,这个资料是徐邦达先生在1992年故宫杂志上发表的论文,上面写:“《功甫帖》藏于上海博物馆,真迹无疑。”我把这些资料,在我浦西馆开馆的时候就弄出了50平米的房子展示,它的左边是上海博物馆说“双钩”的观点,右边是市场上所有艺术品爱好者和收藏家们驳斥他的观点,再过去讲述的是“双钩”的现状,书写是什么现状,我全部放大放在房间里面,作为学术讨论。包括里面还有当年的一些出版物,包括争论的一些报纸文章,我整个差不多有50平米就展示这么一件东西。我心情好展一段时间就收了,心情不好就一直展下去。我认为从去年12月19日,上海博物馆提出来“双钩填墨”这个观点,我感觉“双钩”就会永远伴随上海博物馆。原来我不知道三聚氰氨是什么东西,通过吃有毒奶粉知道了。我感觉到通过《功甫帖》,很多人了解了什么叫“双钩”,这个肯定还是要给上海博物馆留下。刚才讲的是《功甫帖》给我带来的困难。
李阳:皈依佛门与家暴无
我的回答是我想当商人,我想成为一个企业家的老师 7月26日,李阳在少林寺正...